《三国的星空》观影指西
更新时间:2025-10-15 09:02:15
《三国的星空》观影指西
【严重剧透预警】
00解题
本文预设读者群体为,对汉末史事略有了解但不甚清楚,看完电影被正史掺野史的影片内容搞得糊里糊涂,希望能简单区分史实和同人情节,以防止自己的知识体系被电影带跑的观众。“指西”出自影片中曹操反复说的一句话:“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这句话出自曹操答袁绍书,上下文是:“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当时袁绍欲另立宗室刘虞为帝,曹操认为如今只是奸臣当道,皇帝因年幼而被其钳制,匡扶只需除灭奸臣即可,并非皇帝无道导致的国之将亡,因此不同意袁绍的建议。“北面”指称臣,“西向”指西征。当时曹操与袁绍并在河内(今河南焦作、鹤壁一带),董卓屯洛阳,故讨伐董卓为“西行”。
01迁都长安与回到洛阳
迁都长安,事在初平元年(190)二月。这是刘协即位的第一年,在过去的一年中,汉灵帝去世,长子刘辩即位,刘辩之母何太后召其兄大将军何进入朝辅政。时宦官权势巨大,屡兴党锢之祸,与世族群体久已势同水火,故何进掌权后,与世族代表袁绍同谋诛杀宦官,引发洛阳动荡。混战中,袁术烧毁洛阳南宫,少帝刘辩和陈留王刘协紧急出宫避难,至小平津(今洛阳孟津区东北,黄河渡口)为董卓所获,方才重返洛阳。
董卓是汉灵帝之母董太后的同族,长期镇守凉州(河西走廊一带,东抵宁夏,西至敦煌)与羌人作战,此次入京也是应董太后的召唤而至。董卓入京控制局面后,由于何进已死,少帝刘辩的母族失势,而董太后曾亲自抚养刘协,故董卓废刘辩立刘协,以期得到一个更加年幼,亲近自己且易于操控的皇帝。由于董卓起自西北,而洛阳位置靠东,不利控制,加上此时以袁绍为首的东方诸侯兴起讨董同盟,故董卓在纵放兵士大肆劫掠之后,强行迁天子于西都长安,董卓本人则留在洛阳,继续劫掠的同时应对诸侯盟军。影片中曹操与董卓军的第一次碰撞,即发生在这一时期。曹操大败,身为流矢所中,所乘战马也受伤倒地。不过史书中的曹操并未遇到神奇老爷爷,是从弟曹洪将自己的战马借给曹操,才连夜带他脱离险境。
后袁绍联军势大,互相攻伐,董卓放弃洛阳退回长安,初平三年(192)四月,董卓被吕布所杀,董卓的残部李傕、郭汜反攻长安,京城再次陷入混战。李傕挟持天子至其营中,在诸势力斡旋下决定东迁,旋又反悔。长安至洛阳不过七百里,而行程之惨烈即使已经史臣修饰润色,读来依旧触目惊心。
《后汉书·董卓传》:帝步出营,临河欲济,岸高十余丈,乃以绢缒而下。余人或匍匐岸侧,或从上自投,死亡伤残,不复相知。争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击披之,断手指于舟中者可掬。同济唯皇后、宋贵人、杨彪、董承及后父执金吾伏完等数十人。其宫女皆为傕兵所掠夺,冻溺死者甚众。
建安元年(196)秋七月,刘协终于回到洛阳。“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闲。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八月,曹操亲至洛阳,迎天子都许。史载:“自天子西迁,朝廷日乱,至是宗庙社稷制度始立。”
02刘协求雨
《后汉书·孝献帝纪》:(兴平元年194)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七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仓米豆,为饥人作糜粥,经日而死者无降。帝疑赋恤有虚,乃亲于御坐前量试作糜,乃知非实,使侍中刘艾出让有司。于是尚书令以下皆诣省阁谢,奏收侯汶考实。诏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后,多得全济。
这段记载的确是大家在讲汉末故事时鲜少关注到的一段,我也是看过电影才注意到献帝本纪中竟然还保留了这样的细节。不过电影对原文意思有所改编,“洗囚徒,原轻系”是说赦免罪行较轻的犯人,以此展现皇帝的仁德,类似一个小型的大赦天下行为,并非鞭囚出血的人祭。电影设计的求雨情节,看起来更像商周时期的祭祀仪式,让我想起商汤桑林乞雨故事。《淮南子》载:“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翦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即降大雨。”另外,影片中刘协所言“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出自《论语》,但更早的源头亦可以追溯到《尚书·汤诰》中“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之言。影片中刘协亲受鞭刑而大雨骤降的情节,很可能是从商汤得到的灵感。不过即便只看史书记载,也同样能展现出刘协的个人魅力,他虽然只剩下“祭则寡人”这一点点象征权力,但依然尽力救济饥民,甚至能体谅乱世中臣下的不易,虽查出官员舞弊,也并未再兴牢狱。
03种地,打仗与黄犬
影片中,曹操讨董失败,与袁绍势力割席后返回许昌,身边人与他讨论下一步计划,问曰种地,答曰打仗,问曰打仗,答曰种地,使人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在讲曹操在许昌实行的屯田制度。《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曰:“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曹操在许昌屯田养兵及兴修水利运河等故事已有不少学者研究,这里不再赘述。今许昌市博物馆亦有常设展介绍曹操的屯田活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亲至考察。
电影原创角色黄犬“麦子”,是曹操屯田活动的具象化体现。不过史书之中唯有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记载,并无曹操与狗的互动。考虑到电影里大汉忠臣曹孟德设定,这里的黄犬倒总让我联想到秦丞相李斯在遗言中回忆到的那只黄犬。以麦子为名,喜食麦饼的小土狗,代表着曹操曾经亲身经历但又已然远去的和平安定的生活,温暖饱足的少年时代,以及梦幻般无可找寻的大汉盛世。黄犬之死揭开了官渡之战的帷幕,战火最终摧毁了粮食、社稷和生命。放下黄犬,他们拿起刀剑,一脚踏入乱世。
04短歌行
《短歌行》的反复回响,是影片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元素。袁绍以“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劝告曹操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而曹操则将其解释为战死同袍之挽歌。前者来自汉乐府传统,《古诗十九首》有“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等语,它们最终都指向了“为乐当及时”的劝告。后者实际上更多来自曹操的其他作品,例如在著名的《蒿里行》中即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句子,这是曹操感时愍世思想最直接的反映。
《短歌行》的创作时间无可考证,很多演义作品中喜欢将它和苏轼所言“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联系起来,放在赤壁之战的时间段内,学界对《短歌行》的系年,最早也只是万绳楠所说的建安元年(196)。电影将之前移到曹操初起家时是一个颇为创新的构想,两种解读的互相碰撞也非常巧妙地展现出曹操与袁绍的志向冲突。不过从《短歌行》文本本身来看,吊阵亡将士这种解读恐怕多少失之穿凿。《短歌行》以人生苦短兴起忧思,所忧之事在于时无贤才,故以《鹿鸣》之乐迎我嘉宾,以周公吐哺之礼招揽天下贤士。诗中曹操已经自比周公,个人认为更可能是在建安后期拜相封侯以后创作。
05袁绍的玉玺
袁绍有废立之心于史有征,然私刻玉玺实属无据。不过,袁绍的确曾经得到过一枚玉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初平元年190)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太祖拒之。绍又尝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恶焉。”惜字如金的陈寿在这里记述了一个很小的故事,袁绍得到一枚玉印,在和曹操共坐时“举向其肘”,曹操因此“笑而恶焉”,与袁绍自此生出嫌隙。古人衣袖内侧有袋,可以盛物。东晋葛洪的医书名为《肘后备急方》,即是说此书应该被藏于肘后的衣袋内,在情况紧急之时可以随时取出查看。系印于肘后的表述,是系在衣外,还是藏于衣袖口袋内,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可以确定,举印向肘的动作,无论理解成收于袖内,个人占有,还是系于臂上,就任此职,在袁绍此事中的指向都是类似的,即暗示“有意称帝”。裴注《三国志》中在此句引用《魏书》:“太祖大笑曰:‘吾不听汝也。’绍复使人说太祖曰:‘今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天下群英,孰踰于此?’太祖不应。由是益不直绍,图诛灭之。”
晋人对这一故事的理解也可以旁证这一解读。《晋书·张寔传》:“兰池长赵奭上军士张冰得玺,文曰‘皇帝玺’。群僚上庆称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师。”张寔得玺事在德兴三年(315),上距袁绍拟肘之初平元年(190)不过一百余年,他对袁绍行为的理解应该不会相差太远。作为西晋末年占据凉州的一方枭雄,张寔势力此时已经基本与西晋断开联系,随时可以自立政权,但他反对袁本初拟肘事,最终拒绝自立为帝,而是将玉玺送还京师以表忠诚。
玉制印章是皇帝专属之物,实际即所谓天子之“玺”。因而,拥有玉印也即被认为是一种得到天命的象征,尤其在政权不稳定的时代,往往被别有用心者视为帝王祥瑞。袁绍以玉印拟肘示曹操,而曹操表面以玩笑的口吻大笑说“我不听汝”,实际心中对袁绍的不臣之心产生警惕,从此将其视为自己的对手与威胁。至于这份敌意是出于“汉臣”身份还是基于类似的野心,就由各位读者见仁见智了。
《三国演义》中有“焚金阙董卓行凶 匿玉玺孙坚背约”的情节,其来源是《后汉书·徐璆传》的李贤注内容,但对于夺玺之人,又从《三国志》作袁绍,相当于是把两个记在混合起来叙述。袁术夺玺之事于史不合,早已为学者考订。沈钦韩《后汉书疏证》即云:“绍之事在共讨董卓时,其云玉印,不必是传国玺。又术拘坚妻夺之玺,在坚殁后,距讨董卓时已三年。术在淮南,何缘举向曹操?此注合二袁两事为一,最谬。”
06北辰,流星与日有食之
从名字即可看出,《三国的星空》对天文星象颇为关注,身份不详的老爷爷夜观天象,看到荧惑守心,昭示天下大凶;曹操作战时遇日食来助,令对方阵脚大乱。这些情节带有浓郁的天命论色彩,虽出自虚构,但作为艺术加工来说,其实是很难得的一种契合当时人观念的“燃点”设计,学术味道浓郁。电影的核心点题场景,是曹操与刘协策马奔赴许的路上,夜观星空,曹操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刘协只愿做一颗普通的星星发光。问及曹操,曹操回答愿做流星。某种意义上,这段对话也可以认为有史料背书。
《后汉书·孝献帝纪》:“(初平二年191)九月,蚩尤旗见于角、亢。”李贤注:天官书曰:“蚩尤之旗,类彗而后曲,象旗。”荧惑之精也。吕氏春秋云:“其色黄上白下,见则王者征伐四方。”
流星的意象,古今差异很大。今天审美意意义上的流星往往象征耀眼而短暂的辉煌,不过窃以为曹操并不短寿,子孙还承汉立魏,享国四十余年,似乎并不符合流星这个意象。而在汉朝人的语境中,蚩尤旗这样的彗星是征伐之象,流星的现世往往象征地上燃烧的战火。从这个角度来讲,曹操对刘协说自己愿做流星,多少有点地狱笑话……
插播一句,这部电影的名字真的很适合改成“烽火与流星”,可惜已经被远方的萧梁占了,非常遗憾。
07衣带诏
衣带诏事件是演义小说津津乐道的内容,史料中也确有记载。
《后汉书·献帝纪》:五年(200)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
《后汉书·董卓传》: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承遂与刘备同谋,未发,会备出征,承更与偏将军王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结谋。事泄,承、服、辑、硕皆为操所诛。
《三国志先主传》: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会见使,未发。事觉,承等皆伏诛。
《后汉书·献帝伏皇后传》: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6991;,累为请,不能得。
电影中的衣带诏事件被解释为董承与袁绍共同谋划的离间计,曹操与刘协之间的相互猜忌全归于误会,最终大家一致对外抵抗袁绍。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设计。且不论史书中曹操与刘协间很难说有多少君臣情谊所言,单就电影剧情来说,这个情节也导致了刘协形象的扁平化。在三国故事的演绎中,很少有作品会注意到刘协的形象设计,《三国的星空》前后使用批奏疏、祈雨、返洛、退袁等情节,本来已经努力构建起了一个虽年幼但心地善良,背负起家国责任,心系百姓的末世明君形象,这是很好的创新。可是对于这样一个自即位以来就不断辗转于权臣之手,却始终不甘沦落为傀儡,尽自己微薄之力希望兴复汉室的末代皇帝,面对都许以来势力不断成长的曹操,疑惧才是他正常的反应。退一步讲,即便刘协对曹操的猜忌仅仅是出于一时情绪,或许写下诏书后就会很快后悔,但对于力劝天子警惕曹操的左右汉臣而言,他们中的很大一批人无疑是真诚地相信曹操是董卓之后第二个挟君自立的权臣,拿到密诏之后,也一定会努力为之奔走,试图联络四方诸侯解救皇帝。例如,若电影能删掉董承删改诏书的部分,将董承叙述为一个直至被杀都坚信自己在拯救汉朝的真正“忠臣”,或许在后面的相见环节,能刻画出一个更真实更复杂的“曹刘”关系。
END.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上一篇:麻将|没人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下一篇:电梯外是人间,19层内是心狱
 《三国的星空》遇冷,观众想看什么样的三国故事?
《三国的星空》遇冷,观众想看什么样的三国故事? 《三国的星空》观影指西
《三国的星空》观影指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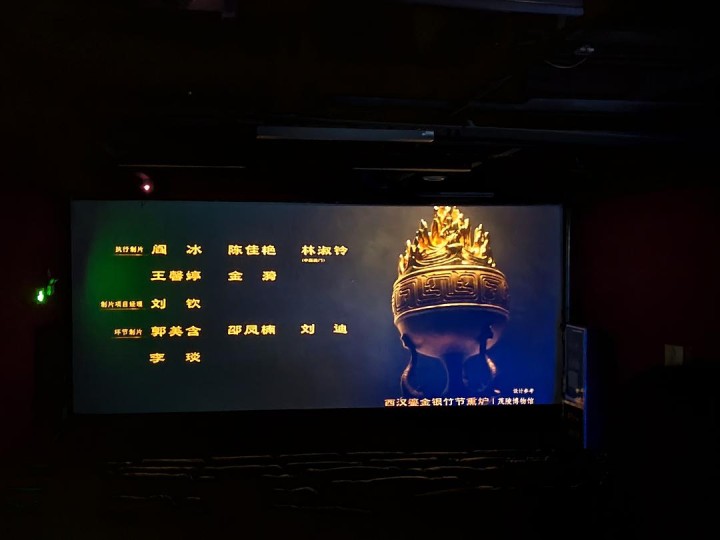 从《三国的星空》展开
从《三国的星空》展开 《三国的星空》说明历史片真难拍
《三国的星空》说明历史片真难拍 定档国庆!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官宣檀健次配音曹操
定档国庆!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官宣檀健次配音曹操 《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定档国庆,柯汶利新片《匿杀》定档12.31
《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定档国庆,柯汶利新片《匿杀》定档12.31